![]() 我的愛戀不含鉛 ( SAN00 )人氣:1495202
我的愛戀不含鉛 ( SAN00 )人氣:14952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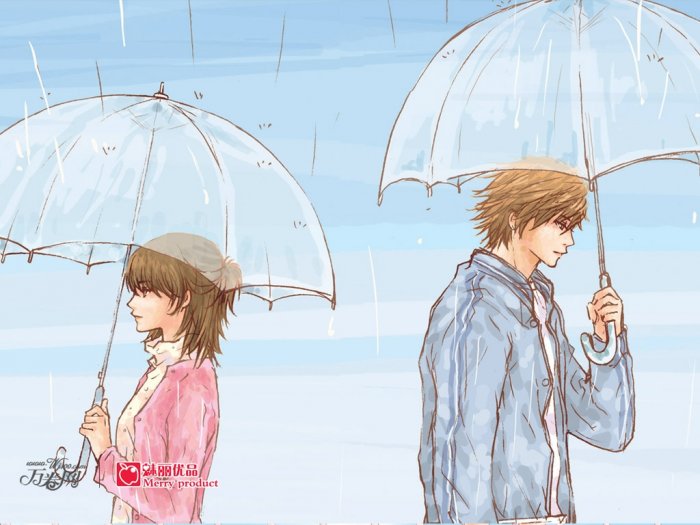
運動場上,幾乎人全走光了。白天會經熱鬧飛揚過,現在,連沉寂也不是;明天朝陽升露,所有被動的生命力勢將蓬勃,經過千萬載,變成了毫無理由。月光下,籃球架彼此相望,單槓並肩排列,任天地默默,一逕地心心相映。她獨自坐在露天長條觀眾席上,空氣中一片深清冷漠的寒,而她並不覺得。
最後幾個借月光打排球的人也走了,迤灑而去,拖著一長串細碎笑語,像尾巴甩過來打疼了她,她懶得抹去臉頰上的淚,黑暗裡,她未必覺到自我存在,何況,也已習慣黑暗,否則該待在哪裏?還有何處可以愈陷愈深。淚水又不由自主流下,什麼都像這淚,全無準備。她出神地笑了笑,整個身體毫不做反應,沒頂之餘,祇會張大了嘴,喊不出聲,像這笑。
那天晚上,她一個人走回家的。意外的是,月光很好,路很遠,沿途有熱鬧也有荒清,像一句話──是非成敗,她的身體空到彷佛不存在,心裏卻陣冷陣熱,寒到透頂時,居然不由自主地大聲叫出:「啊─啊─」像野獸,她知道是自己發出來的,卻一點也不害怕。從他們家出來,忘了拿皮包,口袋裏只有一個銅板,打電話讓人來帶她,錢被吃了──她什麼也不想講,什麼也不想聽,什麼也想不起來,眼前光浮著何毅張臉,碩大無朋,一直在前方笑,他們哭過也鬧過,都不比這刻那般沒有感覺,她筆直朝著那張臉走去。彷彿他又伸手來位她,要她、要她……她一甩臉,臨扭頭看到何毅眼睛裏有些什麼,他有點懊悔了嗎?她從來以為他跟別人不同──再打電話去,他已經走了,什麼話也沒留下,還不如他眼睛裏的表示。
半夜接到他的越洋電話,好遠好假,還不肯說走前已經結了婚。這麼親近過,這麼深沉。是他傷了她,還是她傷了他?
她一直懷疑他根本沒離開臺北,懷疑那天晚上祇不過是夢!.跟著她、牽動她,愈反抗夢痕愈深,他在夢裏吼道:「你到底愛不愛我?」是夢也是現實,他的聲浪太高,變成暴風雨,兩情相悅真是一場暴亂嗎?她的反應偏偏同樣激烈。
她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?只教會她拒絕嗎?
他走後,她終於在天橋上碰到他的好友,這人她找過,某些原因沒再找,是自尊或自信,她不記得了。 : 「何毅走前結婚了!.」那人說。
四周盡是人、車,逼得她更單獨,懸在天橋上。前方的標準鐘是五點,光天化日,她無非是人群中的一個。
「你說什麼?」她完全聽不懂對方的話。
後來想起,一切如此,他們的愛太模糊了,幻化成無邊無涯的沒有重點。
那人也有些遲疑了,不願再說一遍,不說比說了還有別的意思,徹徹底底刺到了她。
原來,就她什麼都不知道,她唯一的愛戀,把她甩得如此遠,她一直當這是鬧意見,他要她不要,過去就好,沒想那晚的爭吵,變成最後一次,然後戛然停止。
就在人海中,眼淚毫無遮攔流了滿臉,從沒一刻,她那麼恨自己舒適的成長環境,她如果有一點點辦法,絕不允許自己哭。她真不相信這是人做得出來的事。
她終於還是回到家裡,整個人比屍體有口氣,所以會流淚、會感覺。她其實恨不得自己
死的,最好從沒活過,除了痛,她根本懷疑自己是活的。
痛到最深,就什麼感覺也沒了。都說長痛不如短痛,不料這也許是一件事。
她幻想何毅再來電話時,要怎麼說。他卻彷彿已經知道結果,半夜裏再沒他的電話,連一句多的話都不必;他那邊是白天,她每天在黑夜中瞪著,可是祇要有電話,她閉著眼睛也能直直抓到聽筒,這動作她太熟了。真可笑,他置她於這地步。
她母親看不過去,要她換個環境;她們家,何毅進進出出數不清多少次。她母親也說不出狠話來,到底人已經要死不活,犯不上真逼出她最後一口氣;就恨她如此不濟!
趁著她母親任教的大學放寒假,宿舍幾乎走空,少數女生留下看書,完全陌生而有人氣,她家裏才放心。她反正單剩下一具身體,由人安排去吧,她們家向不准女孩在外過夜,現在倒放了她。有什麼用呢?無論遠近她都會想,離這事愈遠,可想的來回更長。
她住的那間,有三個人沒走,是人最多的一間,分明是她母親的用心。她處在這中間,卻完全不是她們中間的一個,她們真小,小到看不出歲月的痕路。
每天,她躺在床上等寢室完全空了才起身,先不洗臉,光坐在床上發呆。窗口望出去是運動場,捱牆豆排鳳凰木,不是開花的日子,彷佛心力都枯竭了,不知道在等什麼。操場上永遠有人,聲音老遠被牽引過來,活力被留在原地,所以穿不過大氣和成排的鳳凰木。她想晚上也許會空點,她不要看見人。
浴室在宿舍的最後面,她端著臉盆走過長長的通道,每間寢室門曰排滿了鞋子,凌亂而無力,像場人生,磨練太過。有些寢室關得嚴緊,門上卻貼了各式圖樣,又那麼生氣盎然,有許多辦法似的。彷佛門一開,就會冒生一串如圖樣般的故事;也有半掩閉的門,屋裏閒寂安靜,偶爾傳出幾聲單調的吉他彈得動人情腸的地方,是空白處,勾起她一串淚水。洗臉臺上散放了幾個臉盆毛巾溼淋淋扭在盆裏,主人偷懶,洗完了也不拿走,反正明天還得洗,似乎是人在盆在,卻沒有一個臉盆她認得出主人是誰;她把臉埋在盆裏,水經過太陽地熱,涼人不透,只有她自已使自己發寒。真像她的生活。是因為太熱了嗎?
和剛才在寢室裏同樣的聲浪一陣陣從窗口飄入,彷彿她易地而處,還是那麼從頭到底的一個人,不多也不少,真好笑,她聽得見世界的聲音,她的一切無聲無息,早死了。她不曉得「生命的意意」有何用處,她連想法也沒了。
她到底活了下來,光覺得了一個名字──何毅。
深夜的運動場上有點不甘心的浪漫,個人的牽一髮都像狂舞動全身,她老遠凝望著這個不相干妁畫面,月光下她連影子也沒有似的孤獨;操場風大,把她的落寞吹散到更薄弱,她唯有緊緊抱住身子,緊緊守住自己。
以後呢?愈走離生命愈遠,如果不是因為父母,就更遠了。什麼時候淚水又流滿一臉後滴在地上,她拿自己去灌溉大地嗎?天地不仁,她又是什麼事物的雛形?是愛嗎?
愈坐愈沉,她站起來隨意走走,跑道上有人一圈圈繞著,真傻,費這個力去跑人生做什麼?那人跑遠後又跑近來坐在前方草坪上,理個小平頭,坐下後便動也不動,她真想去間他滋味如何,臨走到那上則面,她繞開了,遠遠的寢室曳出疏落有致的燈火明滅....。
像一個人久念的故鄉或心事,那麼熟悉而情怯;往往如此,可觸不可及也夠了。就這樣,沉沉的凝望著她的最遠也是最近,什麼時候結束呢?這日子什麼時結束呢?她雙手撫臉,又是滿面淚水順著手縫滲出,夜色中無顏無色,她連放聲也不會了。
人車懸空,許多雙詫異的眼睛,她不能動也不能說──
「是妳先交了男朋友嗎?」何毅的朋友試探道。
「啊──啊──」那一直串尖叫從她心裏發出,碰到人體、大樓又撞了回來,把她自己擊潰。
她完全沒料到自己會叫出來──
叫出來就好了嗎?
她放下蓋臉的雙手,深呼一口氣,那片明滅燈火仍在,並非海市蜃樓,偏偏她情緒全無去處,好累好累!.盪在空中,什麼時候才是盡頭?
也不記得是何年何月,也不算自己在宿舍住了多久,周圍又有些什麼人!永遠是這樣的晚上,看不盡的燈火明滅,什麼什麼也想不起來。
偶爾的一天,那跑步的影子她終於看清楚了,並不像那種見面即眼熟的長相。她更熟悉他的背影,和他跑過她身邊時的感覺,那張臉上,長得最好的是鼻梁,筆直挺毅,不容易出軌的面相。他仍然一樣,跑累了,就坐到草坪上,有時候也加入人群中嬉鬧,她想,這種人長大成熟後會是一種什麼樣子?會騙多少女生?
這天,不小心回去早了,寢室裏圍坐了一圈,全盤腿坐在床上,一個室友拍拍床叫她過去坐,並沒有人特別注意她,大家笑著、鬧著、快樂淹沒了一切,屋裏是她多少天來的同伴,雖然彼此每天見面,她一個也叫不出名字,她坐在床沿,臉上光浮著笑,愈坐愈沉,彷彿被快樂沒了頂,想伸頭透口氣!
她走到外面,黑夜吊得老高,沉默無聲,似乎習慣了自己的命運,寂靜中,跑道邊的草皮上盤坐著一個人,清亮的小平頭上橫著樹枝,不猜,也知道是誰,樹下的黑影,就要幻化拈花飛仙而去似的,她反而定下了心口,停住腳步,在那人身後坐住。遠遠地望著對方的背影。
她猛地刺了下:「妳到底要做什麼?」
就在同時,那人突然起身,回頭看了她一眼後慢慢走遠了。那眼神,她看了一震:他認得我嗎?
從來不認識的人,暗中陪她度過一段時間,她最難捱過去的光陰。黑漆中看不見的淚水落在草皮上,抹去了,又泉湧而出,一個晚上到底要想幾回呢?
星夜將盡,東方漸露魚白,這種無法相無休止的夜也可凝視一輪,她獨自清醒,連得意也不是。她起身後在原地站了會兒,鬆鬆發麻的腿,轉身正要走,背後草皮上突然直起一個人,仿佛躺了整夜,是他又轉了回來嗎?他在自己背後盯著嗎?一陣涼意直上脊椎,半絲感覺也沒了。時辰不對,什麼都要變質,他們祇屬於黑暗嗎?四周看得很清楚了,真好像是他。
那人筆直朝她走來,驀地看到一張臉,她整個人驚成個大嘴。
「見鬼了!」他聲音澀澀的,有點乾,晾了一夜似的。
「你試試看,鬼變活人才可怕呢!」
「不壞!挺有神經的,以為真有個人半死了!」
確定是他了,她繼續往前走,沒有心情理會,再回頭,那人仍站在原地,好像她拋他,她冒上一陣酸。她不得不回寢室去,幸好大家仍在夢中,她怕透半生不熟的人,偏偏生人處處便熟,時間真可怕!
她躺下後拉上被子蒙住頭,又是混沌全生,多少天來第一次她睡下以後沒有流淚。整個人被夜風乾了。
「那人為什麼半夜不睡呢?」朦朧中,她試圖開始觸動某些外圍,又什麼都沒想通,思緒處處碰壁,彷彿如鯁在喉,鬱結成塊積在那兒,又來了,那份狂喊的意願再度直往上衝,她縮起又伸直了身子,掙扎著要擺脫什麼,終於在那麼不穩的夢中醒來;天更亮了,一道陽光透過玻璃窗直刺她的眼睛,室內芅亮,房裏空蕩無聲,她突然想起家居的下午或早上,每次醒來都覺得是新的一天,而不是舊的重疊。
她該怪何毅還是自己?她真想知道原因,為什麼呢?長晝夜永,她靜靜的半臥在床,什麼也不做,寧願處於黑夜,期待的日子永遠這般漫長嗎?
她突然發現自己有點眷戀黑夜。她習慣了在星空下遠遠看人群,她走著走著漸漸又恨起何毅,她反反覆覆,何毅知道嗎?他又在哪裏?她獨自跑到完全陌生的寢室裏住下,她認識誰呢?他讓她把自己托付給一群陌生人,這就是他的責任嗎?她連一句都不願意多說。日子一天天過去,那些想法漸漸沉澱下去,她整個人浮在上面,不時,那些想法又翻上來,如同反芻,久了,失去味道,卻更反胃,終究要把人變成垃圾。
她思緒走得愈遠,愈把自己拋下而無力拉回。更遠的,是那個不會回來的人,和愈來愈近的記憶。
她躺在草皮上,什麼都最好別看到,閉久了雙眼,又覺得前面有東西晃動,她睜開眼睛,真站了個人,她照舊驚成一張大嘴。
「奇怪,你怎麼見到我就這表情?」那人說話總有股傻勁。
「你幹麼老偷窺人?」她火了。
「有這麼重要?別神經兮兮好不好?」他輕鬆兩下帶過。
一股清香,隨那人每開口飄送過來,像說出都是動聽的話,愈發讓她火大。
「來,送給你!.」兩朵垂垂老去的曇花,死了也還有花魂,夠英雄一輩子似的。拈在他手上,說不出的勉強。
她皺皺眉,完全說不出話,就覺得荒涼的好笑,突出日就不可抑止;曇花與夜景,一派地老天荒的誓守,讓人想用笑來掩飾什麼。
他一點也不覺得好笑,自顧說道:「曇花開放時還真挑剔呢!非夜半不開,妳說是何道理?」
她刺了一下。
他還是無事的說:「來,來,送給妳,有些人是比較曇花的!」
天地之大,她實在不知道該把自己放在何處,她一把拂開拿曇花的手,想走開,偏動不了,僵直得像那天在人行橋上,不同的是,現在她一滴淚也流不出。
「妳是哪一系的?」他間。
「失戀系!」
他仰頭狂笑後,正色說道:「好系!好戲!」
「你是哪一系?」
「遊戲!」
她又想哭,她到處碰見人,都是成把成抓,她下認識他,不懂得他是真是假,甚至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,明天還見得到見不到都成問題,卻是唯一的一個!她快步走開了,曇花一路香回寢室,是唯一的近身。躺在床上了,還無所不至,彷彿另一種殷勤或關懷。
她猛地直起身子,曇花有香味嗎?那麼是心理作用了?寢室裏又走了一個人,留下來的兩個都還沒回來,她其實也不知道她們的姓名,也不知道她們都到哪裏去。
那份清香無邊香無著地擴大了,.她直起身子,走到室外,操場上還有少數人,一眼就看到了他,在跑道上轉圈子,穩定、自信而安靜,那麼大的操場上,單獨的身影,說明了什麼呢?這人也真不怕。
他停止跑步走了過來,對她說:「沒人表演節目,很無聊吧?」難得的正經。
「你再去表演吧!」
「不表演了,老了,如果妳是褒姒我就再去繞圈子!」
她倒真笑了。他老了?
「沒那麼嚴重,我失過一百次戀,沒什麼了不起。」他突然說。
「輪到你教訓我?!」她歇嘶底里對著他的臉,狠狠叫起來。
「那妳來教訓我吧!.」他仍是一本正經。她在他眼底看到自己的前身,深呼口氣,她安靜了下來,瞪著他半天才說:「我跟你沒有關係!」
「妳放心,我讓妳講完才回嘴,吃點虧沒什麼,學點乖並不那麼悲觀!」
「你究竟要做什麼?」她問,她永遠都處在自問或問人嗎?
「有那麼嚴重嗎?.」他答。
「有!」
「有總比沒有好!」
她沉沉的走回寢室,難得有月光,拖了老長的變形的孤單。
寢室裏,有股奇異的寧靜,像曇花迸放的前刻,寢室裏的人還沒回來,是不是已經走了,她還不知道?她的眼淚潸潸又掉了下來。外面的天空彷彿是個假的展示,無聲無息,一如她的心境,是她的心境嗎?多少人都沒用,她從來不認識他們,陪著你的才是真正的認識。她卻逐漸平諍,像看到他眼底的自己,她誰也不恨。
她又去過操場,足足等了一個晚上,他再沒出現。寒假快過完了,她身上老帶著那股清香,她凝望夜空,自顧笑了笑,早成習慣了不是?天亮後她收好行李準備離開。她想,他沒名也沒姓,她又可以是人海中的任何一個。
她再不用遇見他。曇花開過總算份美麗。